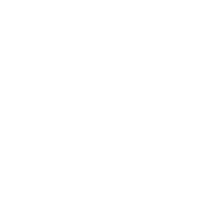2013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院友会一行来到小汤山探望协和妇产科老前辈林崧教授之子林永烈先生。先生是著名野生动物学家,曾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任职,今年80岁了,但精神矍铄。在两小时的交谈中,随着林老绘声绘色的讲述,林崧老前辈的传奇经历,老协和“公用邮票”、“公用铅笔”、铁柜保管、洗衣制度等一个个故事生动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林崧(1905年~1999年),福建莆田人,是我国妇产科病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所著《妇产科病理学》是妇产科病理学的奠基之作。
林崧1932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并留在妇产科工作,后出国深造。1942年初协和关闭后,林崧与卞万年、金显宅、卞学鉴、施锡恩、林必锦、关颂凯等一起到天津创办恩光医院(新中国成立后与几家医院合并组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之后一直在天津工作。
聊天过程中,时年只有五六岁的林老清楚地回忆起1942年协和关闭时的情景:“日本兵站在协和门口把守,只允许医护人员带走私人物品。父亲在医院没别的,就是一些书和从30年代起开始收集的一些切片,这是他最宝贵的东西。父亲把我带到医院帮忙,我把书打开,父亲将切片一片一片塞到书里,再把书一本一本拿绳捆起来,并用蜡封好。后来写《妇产科病理学》用的很多资料就是这么带出来的。”
除了在专业上的造诣,林崧还是著名的大集邮家。他对这一方寸之物产生的强烈兴趣始于1936年公费出国时。林崧一生生活俭朴,因倾心于集邮60多年,所以工资很多都用来买邮票。几十年来,他收集了大量清代以来的各色邮票,所集邮品中稀世孤品极为丰富。新中国集邮史上第一部代表中国参加国际集邮展览的邮集就出自他的收藏,而且第一次参赛就获得了大奖。中国众集邮家中多为邮商,然而林崧则不同,他喜欢研究邮票史,只买不卖。他说:“邮票值不值钱我不知道,我只关心它的历史和欣赏价值。”去世前,林崧将他价值连城的邮票全部捐给了国家。
而此行拜访林老,我们也收获了一个特别的礼物。林老代表全家向协和医院捐赠了一枚由林崧教授精心收藏的老协和邮票。这枚邮票的图案是国父中山先生的肖像,正下方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票面上带有“PUMC”的打孔字母。正当我们好奇地猜测时,林老向我们娓娓道来。原来这是一枚协和在上世纪30年代使用的“公用邮票”,以使职员因工作用途领取后,经收发室审核后发走信件,目的是防止私人挪作他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非常普遍。林老回忆,当时这种做法在协和只是个形式,“协和人不会占公家一点便宜,哪怕是一根铅笔都不会拿回家使。当时协和的铅笔上都印有PUMC的字样,要求不能带出办公室,下班回家后若还要工作只能用自己的笔。如果当时被人看到非工作时间使用带有PUMC字样的东西,就觉得再也没脸见人了!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林老回忆说,老协和的工作人员并不多,但工作却井井有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老协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所有员工都按规章制度办事。
在老协和的家政科档案里,有一套人事管理和清洁流程的规定,对什么地方用肥皂水、用多少浓度都有详细规定。负责人订出排班表,给每个工友定时、定点、定任务,并以严格的标准加以监督考察。当时协和医院的清洁卫生闻名全国,家政科的海丝典护士长还曾专门写过一本清洁管理的小书,很有参考价值。
老协和的洗衣房有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每人衣服上都有一个号码,按时送洗,衣服洗完后,要先送被服处检查,扣子掉了给补上,有小破处补好,破得太大才换新的。污染的和洗净的被服分别从不同通道送取,绝不允许把病人换下来的衣被在病房地上抖开清点,而是装入污衣袋。遇有破旧的被服,由缝纫室修补或改制它用,即使是大小便失禁病人使用过的褥垫、丁字带、尿布等,也绝不随意浪费。
再如保卫制度,那时学生在走廊里都有一个铁柜,用来存放衣服书籍等,要求随时锁好。规定夜班值班人员一定要把每一个柜子的门把拧一下,如发现没锁好,就把里面的东西取走,第二天上交主管部门,再由学生取走。由于这种严密的保卫制度,老协和几乎从未发生过重大失窃案件。而全院的房屋水电管理更是出色,从未听说“长流水”和“长明灯”的情况。

 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手机学习
手机学习